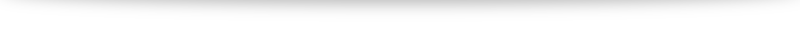狠睡兩天,夜半醒來,只有床頭鹽晶燈微明。當年因總在醫院、學校,法師饋贈,囑放床頭。或許有負離子,也或許有別的作用。初到時,電壓不同,燈泡連連燒壞,換了這的電線與燈,就持續亮著,我離開幾月也不曾熄過。佛教常說點一盞燈,日子久了,燈只是一種象徵吧!
鼠蹊部生了疔瘡,在臺貼狗皮膏藥,膿成的小女已幫我擠出,更深處還有,昨自己擠不出來,繼續貼。臺灣的狗皮膏藥真好。那年帶了一堆過來。學長蜂窩性組織炎居然靠它貼好了。有些東西真好,只是現行法律約束太多,無法傳承發揮。日子久了就見見淹滅了。
媽叮著要常常打電話。我決定,半個月打一次。如果常打就變成習慣。沒空打的時候,她就等電話,接到電話一定生氣罵人。打給她,永遠不會長話短說,重復那幾千遍的別家瑣碎事。電話費浪費在不知所云,講完了就忘了。一通電話費,夠我生活好幾天了。大弟很少打電話,媽總說他孝順。接到他電話總是和顏悅色。
媽常說我們沒給她錢,我算給她聽,我給了多少。實在氣不過了加問一句:你大兒子有給你錢嗎?媽說:沒有。可是他很孝順,知道我喜歡吃,會寄咖啡、魚、水果來。大弟一年根本沒寄幾次,估算起來,還不如我給媽一次紅包的錢。如果我在,買東買西的,哪樣不是錢?大弟是公司主管,每年全家出國旅遊多次,跑的都是歐美澳洲。我貧無立錐之地。她卻一再霸佔我的時間,不讓我有發展。她生病,我陪在身邊照顧,鬧得不像話,我打電話給大弟,叫他過來看一下。她卻說他忙,不要叫他來。媽生病到現在,大弟來過兩次,其中一次是媽過生日,大弟媳從頭到尾沒露過臉。就只在打電話的時候,順便跟爸說轉達:大姊辛苦了!有時我想,這是典型的重男輕女。大弟得寵,連他老婆都不用管事。不由得又想到斜對門的女兒。肝切除了大部,在家打理家務,種菜,照顧父親。還找了手工,每個月賺七千塊,付了水電及一應開銷,剩下的都交給她爸。老頭也真行,一點一點的攢起來,湊到二十萬,就給兒子。在他認為自己很能幹,在我眼裏,他是人渣、吸血鬼。